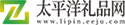刘震云回母校,和北大学生聊了什么?
妙趣横生的表达,引人入胜的故事......当我们谈起“文学”时,总会将其视为生活的凝练和语言的艺术。有一位作家却说:“文学的底色是哲学。”“哲学停止的地方,文学出现了。”
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“小说家讲堂”课堂迎来了当代著名作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友刘震云。他用“量子纠缠”的概念阐释文学与哲学的关系,并在笔耕不辍的人生中坚定不移地践行着。本讲座系“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-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”系列讲座活动之第一讲。
当我们谈论文学与哲学的时候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我们在谈论什么?
讲座开始前,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刘震云先生
“在这个世界上,刘震云只有一个。他有着非常迷人的个性和更加迷人的作品。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,震云先生创造了一大批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,比如《一地鸡毛》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和《一日三秋》。这些以一字开头的作品,一以贯之地表达着他对中国文化核心命题执着的探索和表达。”
——讲座主持人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、作家 李洱
文学的底色是哲学
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,我们孜孜不倦地问过无数位作家:
“什么是文学?”
刘震云的回答是:文学是生活停止的地方。
我们都知道,文学是生活的反映。同一件事,同一个人,同一种情绪,同一个思绪,在忙碌的生活中,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复琢磨,于是将它们轻易放过。生活在此处停止,文学却能够继续延伸,将同一个人,同一件事,同一种情形,同一个思绪展开分析。刘震云认为,那些在生活中忽略的认知和思想,需要文学来体现。
丰富的生活经历能够为他提供文学创作的素材。在刘震云看来,“生活不用体验,生活永远是扑面而来。”近些年来,他有许多新鲜的经历:参加《脱口秀大会4》,做客《向往的生活》,在《文学馆之夜》对谈。此次回到北大,他又与博雅塔合影留念,恍然回忆起自己在母校就读时,全班同学排队在此拍照的场景。凡此种种,皆是他扑面而来的生活,也为他带来无尽的思考与创作。
生活的河流汇入海洋,文学的暗流依旧奔流不休。刘震云认为,对于好的作者而言,文学不仅仅是生活的反映,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。
白居易《卖炭翁》里写道: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。这两句诗中的思辨,令他感受到巨大的哲学力。《琵琶行》中的名句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,也反映了哲学的思想:人们彼此的相知与时间无关,有人白头如新,有人倾盖如故。李白的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相互映照,陈陶的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另辟新境,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更是在一首诗中完成四种时态的转变……刘震云认为,凡是好诗,一定不单是情感和情绪的表达,还要有思辨的含义。
2016年,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位歌手鲍勃迪伦。他最著名的《答案在风中飘(Blowin" in the Wind)》歌词写道:“一座山要伫立多少年,才能被冲刷入海;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,才能获得自由;一个人要回转多少次头,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”几句歌词的蕴意,包含着哲学思考。
抱有“文学的底色是哲学”的坚持,刘震云的作品始终探讨着一个核心的问题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生生不息,在我们的文化基因当中,一定有一个密码,指引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存在于世的信念。这样的文化形态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?这些问题会长久地萦绕在我们心头,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不得不作出严肃的应对。刘震云试图用一部部作品给出答案的启迪。
哲学停止处,文学出现了
文学的底色是哲学,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学写成哲学。
哲学力图解释这个世界,但不能讲清楚人的情绪,人的情感,人的思绪,人的思考和人的灵魂。哲学讲不清的东西,由文学来说。哲学停止的地方,文学就出现了。
这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:“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,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,因为它的原因隐藏得非常之深。”
在刘震云老师最新的作品《一日三秋》中有这么一段:
花二娘在渡口站累了,也坐在河边洗脚,边洗边说,水呀,还是你们讲信用,说来,每天就准时来了。水说,二娘,你昨天见到的不是我们,我们也是今天刚到这儿。花二娘叹息,好在河没变,不然我就没地方去了。水说,二娘,水不同,河也就不同了。天上飞过一行大雁,花二娘说,大雁呀,还是你们守时呀,去年走了,今年准时回来了。大雁说,二娘,我们不是去年那拨,去年那拨早死在南方了。大约等到宋朝徽宗年间,几只仙鹤飞过,又几只锦鸡飞过,花二娘明白等人等成了笑话,这天夜里,突然变成了一座山。这山便叫望郎山。
河流中的水不同,河流就不同,守时的大雁也不再是去年那拨,这样运动变化的思考,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:“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”哲学思想的细节体现。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、变化、发展之中,目光所及之物看似习以为常,却早换了人间。
经过了数十年的文学创作,刘震云发现,语言对于小说的意义并不是最重要的。语言风格和故事的感人度是很容易达到的,而最困难的是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结构,这考量一个作家思辨的能力,更体现了作家身上文学与哲学“量子纠缠”的程度。一些创作者后期的作品并不尽如人意,往往是视野格局、知识广度和思想认识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判断。
在长篇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,刘震云塑造了一群不爱说话的人:卖豆腐的、杀猪的、剃头的、染布的、破竹子的等等,他们平常不大爱说话。不爱说话的人并不是无话说,而是因为他说话不占地方,即说话也没有人听,对话变成了自言自语。说话没人听,久而久之,在尴尬和自嘲的情形下,这群人也就不说话,养成了不爱说话的习惯。他们的话到哪里去了?——被咽下去了。俗话说: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那么,没说出的话也得往肚子里咽。不爱说话,话到了肚子就变成了心事。这万千的心事包含着他们对于社会的改变,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。这样一种人物群像结构和故事结构,背后是对时代变革的思考。
在中篇小说《新兵连》中,刘震云则是通过新兵李胜儿的遭遇,进一步说明小说的人物结构如何考量一个作家的思辨能力。《一日三秋》讲述的是一个人与一群人、一个地域、一个民族之间的关系,这部作品中有一个“介入者”——花二娘。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的私塾先生老汪,则是一个“出走者”形象,因失去小女儿灯盏远走他乡,最后开启了新生活。刘震云十分重视小说中的“介入者”和“出走者”这两类人物,正是这两者间的张力,让作品富有思辨性的哲学意味,意蕴隽永。将人类生活中的情感、情绪和灵魂汇入哲学的思辨中,再通过故事和人物徐徐展开,雅俗共赏。
文学与哲学的穿越、交叉、混合、混沌,这就是量子纠缠。
找到写作的支点
作家常常会遇到的一个经典的提问,对于自己的作品,你觉得哪一部写的好一些?
刘震云回答说,其实我哪一部作品都没有写好。在写每一部作品时,我肯定是想把它写好。但因为我当时没有那个能力。回头再看那些作品时,觉得缺点有很多。当然,缺点并不是坏事,失败也不是坏事,它是写下一步最大的动力。
写作的时候,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支点,能够把这本小说撬起来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写作的支点,有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开头。在刘震云的新写实主义作品《一地鸡毛》中,就用开头的“小林觉得他们家这块豆腐馊了”作为支点,撬动了整个作品的完成。书中描绘了琐碎的日常生活,却能承载起宏大的题材和思考。这正是刘震云写作“支点”的智慧,通过重视细节,从小的范围之内慢慢地积累和发酵起大的题材和判断。
小小的支点,其实是故事核心的主体结构。面对文章修改的问题时,刘震云认为这也是个哲学和灵魂纠缠的过程。在构思找到支点之前,支点是在不断更换修改的;找到了支点之后,能够改变的只有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,是语言细节、情节和准确度,所有的主体的建构是不容修改的。构筑好作品的支点和根基后,修改是为了准确,是为了深入,是为了细致,是为了微妙。
世界上的事情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,无形对于一个人,对于一个民族,对一部作品特别重要。作为职业的作家,我看到无形的东西后边,多少言外之意是文字所承担不了的。但它依然存在,它在缝隙之中,这就是微妙的东西。
刘震云的小说以幽默语言著称,“小说家讲堂”的现场也是笑语盈盈。在他看来,真正的幽默是小说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背后“道理的幽默”。尽管这种幽默感时常挟带着深重的苦难,仿佛人性和灵魂的缝隙中透出来的一丝冷风。
他的小说《温故一九四二》被拍成电影《1942》。故事以一次大旱灾为题材,用透着黑色幽默的笔触,描摹有关这次灾难的事实和记录。
作为我们即将死去的灾民,态度又是如何呢?《大公报》记者张高峰记载:
河南人是好汉子,眼看自己要饿死,还放出豪语来:“早死晚不死,早死早托生!”
面对死亡,不是狂怒、抱怨,而是人与人之间心理的较量。这样的幽默,是从过程结构、人物结构,包括人性和灵魂的缝隙中透出来的一丝冷风。刘震云老师总结说:
喜剧的底色一定是悲剧,悲剧的底色一定是喜剧。喜剧往前走一步就是悲剧,悲剧再往前走一步一定是喜剧。
这种带有辩证意蕴的、残酷的“冷幽默”,是他创作的一大支点,也是小说文本中处理文学与哲学关系的重要方式。
当我们在谈论“文学”与“哲学”时,我们在谈论什么?刘震云有他“量子纠缠”的解释,我们也应当有自己的答案。从文学诞生的那刻起,无论是严肃的“文以载道”,还是荒诞不经的“无厘头”,始终不变的是创作者对自我的表达。正如刘震云所讲的“量子纠缠”一般,当文学与哲学彼此相互作用后,其特性已综合成为整体性质,彼此相容,无法分割。
讲座结束后,刘震云为同学们签名